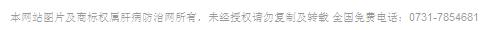福建卢嘉锡科学教育基金会编著的《华夏赤子科教巨擘卢嘉锡》(上下册)年5月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卢嘉锡(年10月26日—年6月4日),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结构化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宗师,我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者之一,中国农工民主党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
本书由卢嘉锡生平画传和卢嘉锡本人部分文稿,及一系列纪念文章等共同组成。以翔实的史料、富有生活气息的文字记述和大量珍贵的照片,全面、生动地再现了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卢嘉锡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竭智尽力,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不懈追求、无私奉献的人生历程。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今天,我们从书中采撷几朵“小花”,再现一代巨擘鲜为人知的一面,算作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文革”中的磨难与抗争
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接着,全国城乡开始“社教四清”运动。年7月,卢嘉锡被派到福州第二化工厂参加社教,年4月结束回到物构所。
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紧接着,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大串联、炮轰各级党委。卢嘉锡和全国众多干部一样,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真诚地希望赶上时代的步伐,可总是跟不上形势。年秋天他给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儿子写信,说“就连叶飞(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的老革命家,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如果不是他亲自检查说的,我真看不出来。”可见当时他心中的惶惑。不久,卢嘉锡作为物构所的党员所长、全所唯一具有高级职称的老专家,理所当然地被扫进了“牛棚”。
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卢嘉锡吃过早饭,就去打扫研究所实验大楼,直到临近中午才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就像搞科研一样,卢嘉锡劳动是很认真的,四层大楼的每间厕所,都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了除去多年的尿垢,他用刷子刷,每个星期都要用坏两三把刷子。一些边边角角刷子刷不到,他甚至用手指甲去抠。即使这样,还是有“造反派”鸡蛋里面挑骨头,贴出大字报说他“劳动态度不好”。卢嘉锡的小女儿紫莼对此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年盛夏的一天,学校早已因‘文革’而停课,刚满10岁、从小就爱唱爱跳的我在家无聊至极,跑进研究所实验大楼,想到二楼的梯形教室看‘宣传队’排练。刚拐进二楼走廊,我猛然停下了脚步,因为我看到一个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身影。那正是父亲,只见他左手提着畚斗,右手拿着扫把,非常仔细地清扫走廊过道。福州的夏季很热,原本就怕热、爱出汗的父亲更是大汗淋漓。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去脸上的汗水,然后整整齐齐地将手帕叠好放回裤兜里,继续他的‘工作’。父亲穿戴整齐、不改学者风度,可他怎么就成了清洁工了?!我无法接受眼前这一幕,呆了片刻后掉头跑出大楼,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愿再迈进那座大楼一步。”
下午和晚上,卢嘉锡就在家里愁眉苦脸、冥思苦想,写检查交代材料。他真诚地反思、检讨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尽地“提高思想认识”、“上纲上线”、“深挖封资修思想根源”。但是,他对“审查”、外调时问他一些别人的事情,坚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忘了就是忘了,从不含糊。卢嘉锡因父亲突然去世、家境困难,从年起曾当过4年中学兼职教师,教英语和数学。其间曾到福州参加过一个月的中学教师暑期培训兼“军训”。“文革”中有专案组来调查某些参训教师的背景材料。卢嘉锡再三回忆,告诉们:“想不起来了。”专案人员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材料,竟拍着桌子训斥他:“你不是说自己记性很好吗,为什么想不起来?”
卢嘉锡回家伤心地对孩子说:“我当老师从来没有对学生拍过桌子,没想到今天这些年轻人竟然对我拍起桌子来了。”他又说:“我是说过我的记性好,但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化学是我的专业,平常多留心,就记得牢;有些事情没放在心上,当然就记不住了。再说,参加‘暑训’的教师来自各地各校,一个月后又各奔东西;不用说许多人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记得住名字,也不知道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呀!”
这场“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卢嘉锡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他被迫每天把时间花在打扫卫生和写检查上。更使他心痛的是结构化学研究课题被取消,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被封存,他辛辛苦苦培育起来的科研队伍,从到年,分几批几乎全部下放到福建省各地的工厂和农村。卢嘉锡一手创建的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被拆得七零八落,剩余的部分被改名为“所”、“划归地方”,不再属于科学院。有人甚至把当年卢嘉锡带领青年科研人员清理坟山、平整土地,用辛劳和汗水建设起来的物构所看做是一块宝地,要把它改成疗养院。有什么能比这让他更伤心呢。
一直到年秋天,卢嘉锡的个人境遇突然有所好转。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一次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科学家、卢嘉锡早年留学美国时的好友,在谈话时他们问起卢嘉锡的情况。总理记住了这件事,会见后立即让秘书去了解,并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指示:“立即解放、安排工作”。此后,卢嘉锡虽然还没有被正式宣布“解放”,更没有得到工作安排,遭批判是少不了的,但至少是不必再劳改扫厕所、挂着牌子陪人挨斗了。
(二)据理力争,中国取得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合法席位
年8月下旬,卢嘉锡率中国化学会代表团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第21届学术大会。随后又前往瑞士的达沃斯山城参加IUPAC第30届代表大会并列席理事会会议。其间,他与IUPAC主席协商,就联合会章程一些条文的解释取得一致;又和参加大会的台湾地区化学会代表团成员、台湾大学陈发清教授(台湾省籍人士)友好交流,并与台湾代表团实际决策人王纪五(台湾“国科会”官员)多次协商、反复交涉,达成谅解。在9月3日的大会上,IUPAC主席郑重宣布,接受中国化学会作为代表全中国的化学会组织加入IUPAC;而“位于中国台北的化学会(ChemicalSocietylocatedinTaipei,China)”以单独财务结算的地方性学术团体身份保留会员资格。随后举行了中国化学会正式参加IUPAC的签字仪式。这标志着我一级专业学会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地区专业学会席位问题基础上参加国际组织取得了重大突破。台湾方面参会的刘兆玄教授(后曾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事后也说:“由于IUPAC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中是数一数二的大学联,它在两岸代表权的处理决定具有指标性意义。事实上,此次达沃斯大会的决定,确为此后一段时间内其他科学学联提供了效仿的模式。”
(三)患难夫妻?一世恩爱
卢嘉锡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妻子吴逊玉与他青梅竹马,婚后夫妻恩爱,同甘共苦50余年。
吴逊玉原名吴盛敏,新式小学毕业后,父亲把她送进在厦门负有盛名的“留种园”私塾,想让她读点四书五经,将来能够知书达礼。吴盛敏天资聪敏,又肯用功,深得塾师卢东启喜欢。卢东启夫妇膝前无女,于是将她收为义女,并取了“逊玉”这个名字。卢嘉锡此时正上中学,回家时常常帮父亲批改作业、帮着辅导学生,因而也与父亲的弟子们很熟。吴逊玉生性好胜,写起作文来总是精益求精,经常得到批改作业的“小先生”卢嘉锡的好评。由文及人,两人相互产生了好感。
年3月8日,吴逊玉身披洁白的婚纱,与身着黑色礼服的卢嘉锡举行了在当时来说算是新派的婚礼。不过“吉日”是卢嘉锡的大哥卢雨亭择定的,他说这天是农历二月十五,俗称“百花生日”。
新婚的日子是甜蜜的,一年之后,爱情的结晶——他们的长子嵩岳呱呱坠地。但甜蜜的日子却是短暂的。就在这年春天,卢嘉锡前往南京,再次冲击中英庚款留学考试,终获成功。8月17日,卢嘉锡搭轮船离开上海,9月24日抵达伦敦,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中英庚款的期限是3年。吴逊玉带着半岁大的孩子留在厦门,等待着夫君3年后学成归来。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待竟然是漫长的8年时间。
年5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厦门本岛,吴逊玉陪着婆母和全家人一起避居当时号称“万国租界”的鼓浪屿,租住在泉州路上的“宁远楼”。但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鼓浪屿,吴逊玉只好带着孩子再逃往闽南内地。卢嘉锡在国外省吃俭用,将节余的奖学金寄回国内供妻儿生活。可是战争期间,寄回的钱款往往不能按时送达,还经常遭到克扣,甚至无缘无故半途丢失。为此,她只好去当电话接线生和农村小学教师,以维持生计。吴逊玉的父亲吴金波原在英资太古洋行供职,厦门沦陷后洋行关闭,他失业在家,也无法接济逊玉母子。实在无计可施时,吴逊玉只好带着孩子去挖野菜,除了自家充饥外,还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钱以维持生活。
就这样一直熬到抗战胜利,在国外8年、学有所成的卢嘉锡回到国内,全家得以团聚。那时候,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即使卢嘉锡是著名的教授,还兼了系主任,但每月的工资也只够一家子半个月的开销。终于有一天,家里没米下锅了!吴逊玉不得已偷偷拿出当年与卢嘉锡结婚时订做的一对戒指,变卖后换回一些大米。卢嘉锡对此事非常痛心,一直到晚年,他还对子女们讲起这件事:“戒指上刻着我和你们妈妈两个人的名字呀!可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也不富裕,打的那对戒指很小,换回来的米也只够吃几天。”
吴逊玉几十年如一日站在卢嘉锡的背后,默默无闻地替丈夫管好家,让他毫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做好工作。他们两人是在年3月8日结婚的,卢嘉锡后来经常十分感慨地对人说:“本来三八妇女节是妇女解放的日子,可是我却是在这一天把逊玉束缚起来的。”这段话也深含着卢嘉锡对吴逊玉一辈子辛劳的愧疚之情。让吴逊玉感到欣慰的是,丈夫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令人尊敬的教育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儿女们也都靠自身努力拼搏开辟各自的事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年卢嘉锡全家迁到福州。当时正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福州工资类别本来就比厦门低,卢嘉锡又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降低了工资,收入一下子少了一截。再加上居民减少了粮油定量,副食品更是十分匮乏。此时的吴逊玉得了浮肿病,可是还在为日夜工作繁忙的丈夫和正在上中小学的子女们的成长操劳。当时福州大学把家属宿舍楼前的空地按每人一厘地的量分给各家种点瓜菜,以弥补粮油之不足。邻居们见卢嘉锡工作繁忙,吴逊玉患有浮肿,孩子们又小,就提出由他们帮着耕种。卢嘉锡谢绝了邻居们的好意,吴逊玉买来锄头等工具,带着家里4个10岁上下的大孩子利用周末翻土整垄,种上红薯、玉米、空心菜和豇豆。
卢嘉锡偶尔得空,也和妻子儿女们一起到菜地里转转,但除了能帮着浇浇水之外,他在这方面确是一窍不通,只能再三嘱咐大家要多向那些来自农村的家属请教。当妻子和孩子们用自己收获的红薯煮了卢嘉锡喜爱的番薯粥端上饭桌时,他很是高兴,打趣地说:看看,你们还是很能干的嘛,我们现在和校主一样了(卢嘉锡一直尊称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先生为“校主”。陈老先生尽管贵为华侨领袖,曾经富甲东南亚,却一生极为简朴,长年食用番薯粥和酱菜)。
得过浮肿以后,吴逊玉身体一直不好。“文革”当中,卢嘉锡进了“牛棚”,“造反派”跑到家里逼迫吴逊玉与夫“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她与丈夫从小青梅竹马,又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她了解丈夫、相信丈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造反派”的无理要求,但却因此成天担惊受怕,又不愿意让正身处逆境的丈夫思想上增添新的负担,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身体终于垮了。经诊断,她患的是脑膜瘤,多方求医都不见好转。年春节,吴逊玉病情危重,此时卢嘉锡刚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不久,正好回福州度假。他沉痛地对孩子们说:“现在形势好了,你们的妈妈却不行了!”说罢失声痛哭。
在组织的关怀下,吴逊医院治疗。当时,卢嘉锡工作十分繁忙,特别是那几天正在召开研究办院方针的科学院工作讨论会。但他还是向中央请假专程赶到上海。手术前,他亲自和医生研究方案,日夜陪护、安慰着妻子。手术当天,他亲自送妻子进手术室,并在门外守候了6个多小时,直到妻子手术结束回到观察病房。3天后妻子渡过了危险期,卢嘉锡才匆匆赶回北京并主持了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的最后一天会议。
在上海手术结束后,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估计这一刀可以管用10年,但由于吴逊玉患的是“地毯式”瘤,附着在脑细血管的部分不可能清除干净,残存的瘤组织几年后还会复发。这话不幸被言中了!从年起,吴逊玉又开始间或出现神志不清的症状。年3月8日,卢嘉锡与吴逊玉这对恩爱夫妻庆祝了他们的金婚之喜。由于吴逊玉病情不断加重,她于年初夏回到福州,从此卧床不起,直至年9月30日与世长辞。妻子去世后,卢嘉锡流着眼泪为爱妻写下挽联:“佐夫君学成功遂同甘共苦诚贤内助?育后代五男二女勤劳俭朴念我慈亲?懿德可风”,并对子女们说:“都说夫妻同甘共苦,可是我和你们的妈妈结婚50多年,共苦的时间多,同甘的时间太少了!”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tzdgt.com/dynmllcbx/5481.html